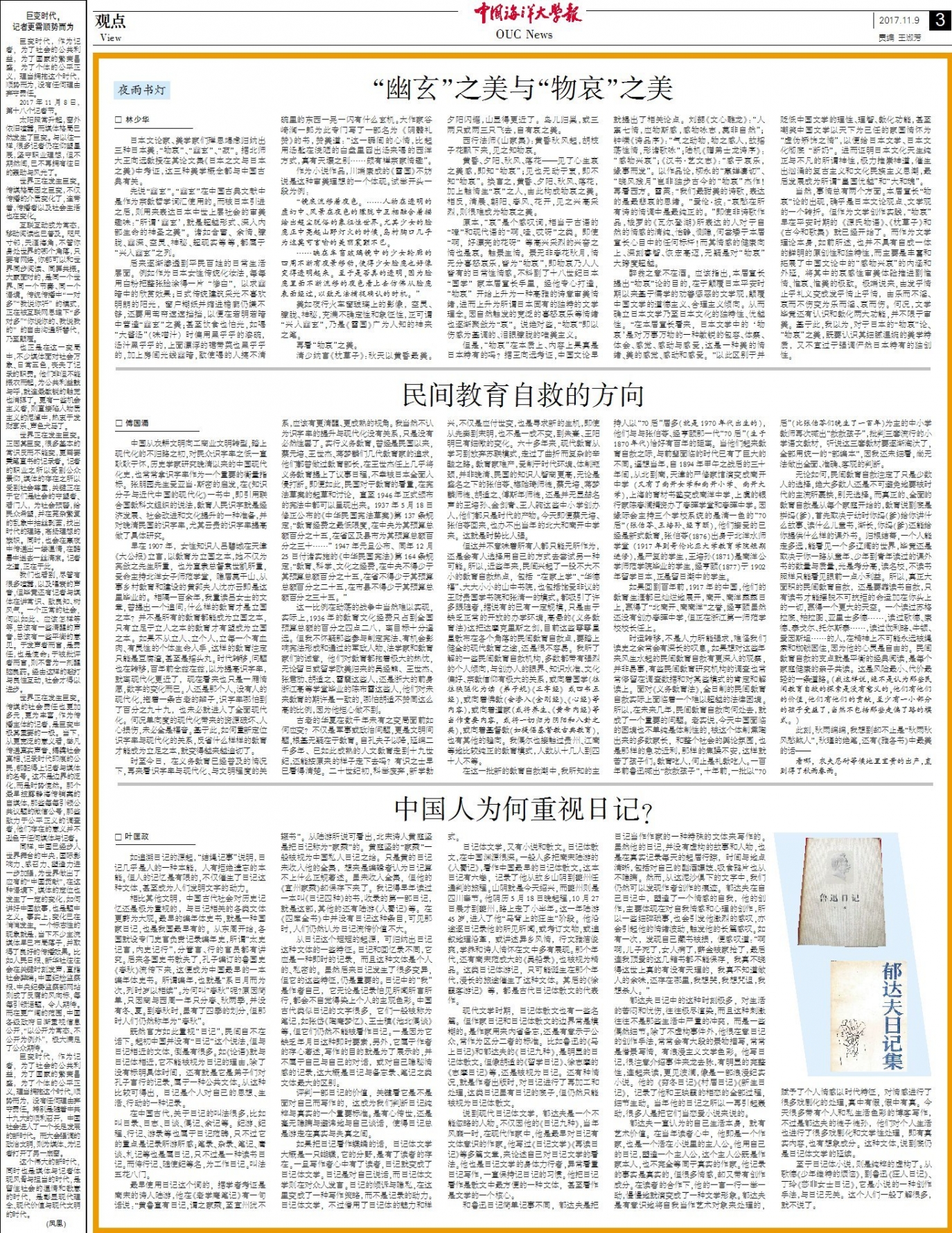
“幽玄”之美与“物哀”之美
期次:第1995期
作者:林少华 查看:12
日本文论家、美学家们殚思竭虑归纳出三种日本美:“物哀”、“幽玄”、“寂”。据北师大王向远教授在其论文集《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》中考证,这三种美学概念都与中国古典有关。
先说“幽玄”。“幽玄”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是作为宗教哲学词汇使用的。而被日本引进之后,则用来表达日本中世上层社会的审美趣味:“所谓‘幽玄’,就是超越形式、深入内部生命的神圣之美”。诸如含蓄、余情、朦胧、幽深、空灵、神秘、超现实等等,都属于“兴入幽玄”之列。
后来逐渐渗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层面。例如作为日本女性传统化妆法,每每用白粉把整张脸涂得一片 “惨白”,以求幽暗中的欣赏效果;日式传统建筑采光不喜欢明朗的阳光,窗户糊纸并缩进檐廊仍嫌不够,还要用苇帘遮遮挡挡,以便在若明若暗中营造“幽玄”之美;甚至饮食也怕光,如喝“大酱汤”(味噌汁)时偏用黑乎乎的漆碗,汤汁黑乎乎的,上面漂浮的裙带菜也黑乎乎的,加上房间光线幽暗,致使喝的人搞不清碗里的东西一晃一闪有什么玄机。大作家谷崎润一郎为此专门写了一部名为 《阴翳礼赞》的书,赞美道:“这一瞬间的心情,比起用汤匙在浅陋的白盘里舀出汤来喝的西洋方式,真有天壤之别……颇有禅宗家情趣”。
作为小说作品,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不妨说是这种审美理想的一个体现。试举开头一段为例:
“镜底流移着夜色。……人物在透明的虚幻中、风景在夜色的朦胧中互相融合着描绘出超尘脱俗的象征性世界。尤其少女的脸庞正中亮起山野灯火的时候,岛村胸口几乎为这莫可言喻的美丽震颤不已。
……映在车窗玻璃镜中的少女轮廊的四周不断有夜景移动,使得少女脸庞也好像变得透明起来。至于是否真的透明,因为脸庞里面不断流移的夜色看上去仿佛从脸庞表面经过,以致无法捕捉确认的时机。”
美如夜行火车窗玻璃上的影像,空灵、朦胧、神秘,充满不确定性和象征性,正可谓“兴入幽玄”,乃是《雪国》广为人知的神来之笔。
再看“物哀”之美。
清少纳言《枕草子》:秋天以黄昏最美。夕阳闪耀,山显得更近了。鸟儿归巢,或三两只或两三只飞去,自有哀之美。
西行法师《山家集》:黄昏秋风起,胡枝子花飘下来,见之知物哀。
黄昏、夕阳、秋风、落花——见了心生哀之美感,即知“物哀”;见也无动于衷,即不知“物哀”。换言之,黄昏、夕阳、秋风、落花,加上触情生“哀”之人,由此构成物哀之美。相反,清晨、朝阳、春风、花开,见之兴高采烈,则很难成为物哀之美。
原本,“哀”是个感叹词,相当于古语的“噫”和现代语的“啊、哇、哎呀”之类。即使“啊,好漂亮的花呀”等高兴采烈的兴奋之情也是哀。触景生情。景无非春花秋月,情无分喜怒哀乐,皆为“物哀”,即物哀乃人人皆有的日常性情感。不料到了十八世纪日本“国学”家本居宣长手里,经他专心打造,“物哀”开始上升为一种高雅的诗意审美情绪,进而上升为所谓日本固有的独特的文学理念。因自然触发的宽泛的喜怒哀乐等情绪也逐渐聚敛为“哀”。说绝对些,“物哀”即以伤感为基调的、泪眼朦胧的唯美主义。
但是,“物哀”在本质上、内容上果真是日本特有的吗?据王向远考证,中国文论早就提出了相关论点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:“人禀七情,应物斯感,感物咏志,莫非自然”;钟嵘《诗品序》:“气之动物,物之感人,故摇荡性情,形诸歌咏”;陆机《赠弟士龙诗序》:“感物兴哀”;《汉书·艺文志》:“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”。以作品论,柳永的“寒蝉凄切”、“晓风残月”岂非独步古今的“物哀”杰作!再看西方。雪莱:“我们最甜美的诗歌,表达的是最悲哀的思绪。”爱伦·坡:“哀愁在所有诗的情调中是最纯正的。”即使非诗歌作品,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所表达的人对于自然的情感的清纯、怡静、恻隐,何尝矮于本居宣长心目中的任何标杆!而其情感的健康向上、深刻睿智、恢宏高迈,无疑是对“物哀”大跨度超越。
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应该指出,本居宣长提出“物哀”论的目的,在于颠覆日本平安时期以来基于儒学的劝善惩恶的文学观,颠覆中国文学的道德主义、合理主义倾向。从而确立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的独特性、优越性。“在本居宣长看来,日本文学中的 ‘物哀’是对万事万物的一种敏锐的包容、体察、体会、感觉、感动与感受,这是一种美的情绪、美的感觉、感动和感受。”以此区别于并贬低中国文学的理性、理智、教化功能,甚至嘲笑中国文学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为“虚伪矫饰之情”,以便给日本文学、日本文化彻底 “断奶”。进而证明日本文化天生纯正与不凡的所谓神性,极力推崇神道,催生出汹涌的复古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思潮,最后发展成为所谓“皇国优越”和“大和魂”。
当然,事情总有两个方面。本居宣长“物哀”论的出现,确乎是日本文论观点、文学观的一个转折。但作为文学创作实践,“物哀”早在平安时期的 《源氏物语》、《枕草子》和《古今和歌集》就已经开始了。而作为文学理论本身,如前所述,也并不具有自成一体的鲜明的原创性和独特性,而主要是丰富和拓展了中国文论中的“感物兴哀”的内涵和外延,将其中的哀感性审美体验推进到惟情、惟哀、惟美的极致。极端说来,由发乎情止乎礼义变成发乎情止乎情,由乐而不淫、哀而不伤变为乐而淫、哀而伤。何况,文学毕竟还有认识和教化两大功能,并不限于审美。基于此,我以为,对于日本的“物哀”论、“物哀”之美,既要认识其细腻温婉的美学特质,又不宜过于强调俨然日本特有的独创性。